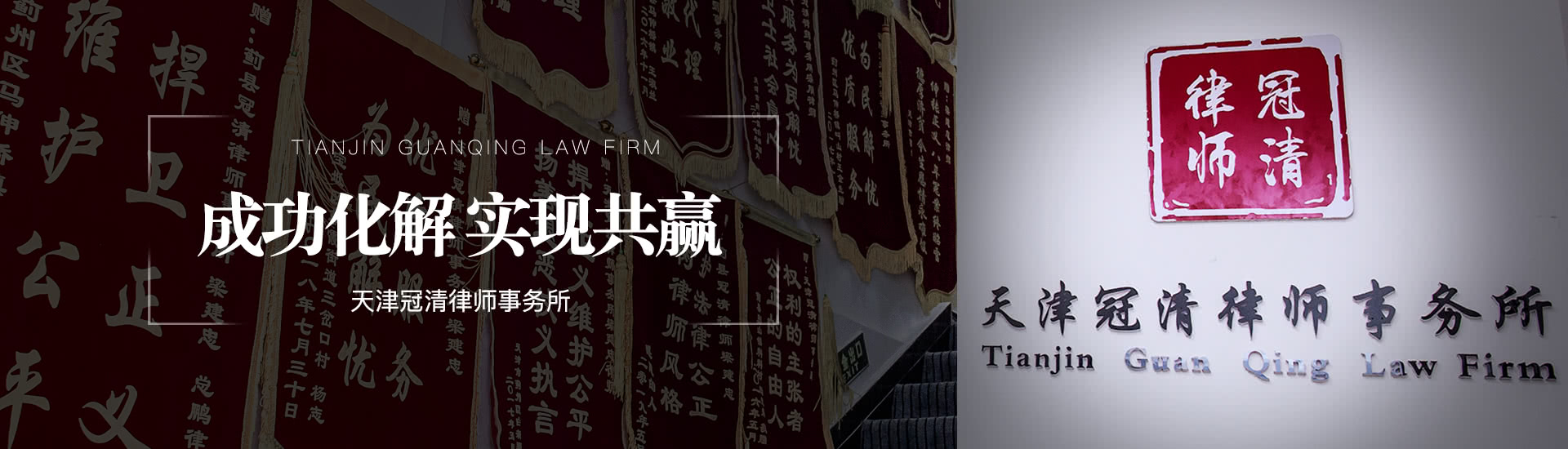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基于不正当男女关系获得他人的金额较大财物赠与的行为违反公序良俗,占有该财物无合法依据,依法应予返还。
双方在恋爱期间,难免有共同生活花销的支出,恋爱中的情侣为对方负担部分日常开支,是表达爱意的一种行为,属于为维系和发展双方感情的正常自愿付出,故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决定对于单笔金额2000元以下(包含本数)的转账,视为赠与行为,不应予以返还并无不当。
诉讼请求
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款项299387元并支付利息;
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由被告承担。
一审查明
周某于2015年11月26日离婚。周某与曾某双方于2018年9月认识,后发展成为恋爱关系,2024年6月分手,该期间曾某尚在婚姻存续期间。周某表示其系打零工,做泥水工,曾某表示其工作为烟酒茶销售,双方恋爱期间,双方约会主要是在外开宾馆,双方家长并未见面,也并未有过订婚。
另,关于双方恋爱情况:周某表示双方三天左右就见一次,曾某一直声称是离婚的,其一直想与曾某结婚,但是曾某不同意。曾某不认可其意见,表示365天中360天都是在一起,其一直与其老公居住在一起,周某从认识曾某开始就知道其有家庭,周某陈述其想与曾某结婚都是胡编的。曾某就该意见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视频(视频中,沙发上坐着一名女性,有一男声说话,内容主要为“有转账记录,这个钱要得回来的……我走法律程序这个钱要得回来的”)及录音(时间2024年7月22日),分别证明周某与其前妻离婚不离家,且共同生活,及周某知晓曾某的婚姻状况,录音中提及了曾某丈夫刘某,据此,视频无法证实周某离婚不离家,曾祥在明知周某不离家的情况下,仍然与其发生恋爱关系,该关系违背公序良俗,是无效的民事行为,曾某基于该关系取得的财产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返还,周某表示知道刘某名字无法证明其知晓曾某婚姻状况。自2019年6月26日起至2024年6月3日,双方存在密切的经济往来,双方均未有转账时涉及转账用途的相关记录。双方均向法院提交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及周某向法院提交银行流水,曾某提交支付截图。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显示双方交易笔数较多,金额不具有规律性,部分转账有表达恋人之间爱意的特殊备注,绝大多数转账则无任何备注。
关于转账的性质,原告认为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现双方已经分手,故应当由被告进行返还,且转账给被告的款项包含了被告借款、网贷、车贷及孩子费用。被告则表示以上转账发生在双方恋爱期间,是双方恋爱期间的消费及过节的情谊表达,用于双方吃饭、娱乐等开支。
2024年12月26日,在双方分手后,周某向曾某发送微信:“我想要,把我的钱拿到手,我就要我钱”,曾某回复:“你想拿多少钱嘛”“现在我给你讲,好多钱我也没得钱,主要是我现在没得钱,晓得不?主要是你想要一个,你想要多少,然后我以后努力一点”“协调以后,以后努力挣钱啊”。曾某表示,该聊天记录系在周某在代理人的诱导下进行陈述,并非在案件发生过程中的事实。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微信支付电子凭证、银行流水、截图、报警回执、微信聊天记录、离婚证、离婚协议等证据在卷佐证且经庭审质证,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事实,综合原、被告之间的诉辩称意见,双方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周某与被告曾某恋爱期间向被告曾某转账的款项是否构成附条件的赠与;2.被告曾某是否应当向原告周某的返还款项及支付利息。
关于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八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根据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本案中,原告主张案涉款项系共同生活、缔结婚姻为目的,系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本案中,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条、第七条、第六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曾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某偿还111866元及利息(利息以尚欠款项为基数,从2024年7月10日起按照年利率3.45%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周某的其余诉讼请求。
上诉意见
周某上诉事实和理由:
2024年年初上诉人才知晓被上诉人一直都有家庭、而一直找各种理由不与上诉人结婚,由于被上诉人的个人原因致使上诉人期待结婚的美好愿望不能实现,双方于2024年6月分手。分手后,上诉人多次找被上诉人索要其在此期间转账给被上诉人的款项,被上诉人也承认愿意偿还,只是现目前没有钱还给上诉人。根据一审开庭审理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离婚证、离婚协议、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银行流水、电话通话录音、视频等证据材料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具有充分完整的证明能力,双方之间形成了附条件的赠与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依法应当向上诉人全额返还款项及利息。其一,一审法院仅支付2000元以上的转款系附条件的赠与予以返还,2000元以下的500元、800元、1000元、1500元、1800元等认定为恋爱消费、娱乐消费等与事实不符,2000元以下的转款金额达六七万之多;其二,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主张的酒款在本案中予以扣除没有事实和法律关系。尽管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交了部分酒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本案系附条件赠与合同法律关系,在被上诉人没有提起反诉的情况下不能在一个案件中同时处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酒款的问题应当由被上诉人另行提起诉讼进行处理,一审法院无权就酒款问题在返还附条件赠与款项中扣除。
曾某答辩称:周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其所称以与曾某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交往完全是不真实的,其自始至终与其前妻都是离婚不离家的状态,且自始知晓曾某的婚姻状态,我方一审也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证实,故双方是不正当的婚外男女关系,其在交往过程中的转账行为是用于维持该不正当关系,且用于双方约会消费,因双方关系违背公序良俗,周某的诉请不应当得到支持,其余意见以我方上诉状为准。
曾某上诉事实和理由:
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结果既未兼具社会效果,其法律效果也严重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具体分述如下:
一、本案现有证据完全能够证实周某离婚不离家的事实。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周某离婚不离家的事实”是错误的,直接影响到认定周某主张“以结婚为目”的虚假陈述。
(一)一审判决书(第5页)事实认定明显前后矛盾和错误。第一:根据我方提交的视频证据显示,周某在与上诉人分手后,为向其前妻表忠诚,说到“律师说过,有转账记录,这个钱要得回来的…”,如果不是离婚不离家状态,二人商议向上诉人要钱的行为又作何解释?第二:周某谎称交往的目的是和曾某缔结婚姻,但是双方交往的6年期间,双方既未互见家属、未商议过任何订婚、结婚事宜、也从未共同居住,仅是频繁的在外约会!这明显与其所谓的结婚目的不相符!也与普通大众认知的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关系不相符!第三:双方均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清楚的认知,上诉人从始至终并未欺骗过周某,周某也没有证据证明曾某欺骗或者隐瞒过其婚姻状况!第四:周某是基于双方不正当恋爱关系向曾某进行转账,目的是维系不正当男女关系,就是一般赠与而非附有任何条件,更非是曾某基于其他不正当理由向其索要!
(二)一审判决认定周某系以“结婚为目的”继而与上诉人交往和转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周某与其前妻虽离婚后仍然共同居住与生活,其离婚目是在于规避拆迁安置增加安置户头,并非其真实的离婚意愿,也更非是与上诉人结婚为目的恋爱关系和交往;其次,上诉人有家庭育有子女且处于稳定状态,周某是明知的,如若像一审判决认定的周某以与上诉人结婚为目的的交往,则属于鼓励纵容第三者破坏婚姻家庭。第三、“以结婚为目的”仅是周某单方陈述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一审判决以推定事实的方式认定“结婚目的”完全有违公序良俗。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从法律关于赠与相关规定,结合本案基本事实,即便周某转账差额在双方共同消费后确有部分剩余,主张返还同样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
1、赠与人的撤销权包括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两种,本案属于任意撤销权。
2、行使撤销权时间条件为赠与标的物尚未交付或未移转登记,本案所涉赠与标的物为货币特殊种类物,一旦发生占有转移就发生所有权转移。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条规定,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双方交往六年多时间,周某撤销权因过除斥期间已归于消灭。结合本案案情,一审判决撤销并返还的11万余元金额也并非是最近年微信转账高于2000元限度的金额相加,一审判决认定周某享有撤销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三、本案不属于“附条件赠与”及“附义务赠与”行为。周某“以结婚为目的”赠与和本案事实不符。行为人应遵从伦理道德、公序良俗。周某自己有家庭且其明知上诉人已有家庭,基于非法不正当婚外情关系实施的行为均应受到法律和道德否定性评价,周某对其赠与法律后果应当自行承担。当不正当交往关系断绝后上升到法律层面给予保护有违社会公序良俗。
1、双方不正当婚外情期间赠与人明知受赠与人处于已婚状态,原告所称意欲建立婚姻关系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且严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和道德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该赠与所附的结婚条件自始至终不能实现,其赠与行为不属于赠与合同法定撤销的情形不属于法律上规定的附义务赠与。
2、建立在“婚外情”这一特定条件下的赠与行为,其目的具有不正当性,违背社会公德,已经对社会道德体系带来了不良影响,对已婚一方的配偶、家庭都有极大的伤害,上诉人曾某现在勇于对抗被上诉人的暴力胁迫,断绝不正当关系,回归家庭的态度应当予以肯定。被上诉人提起本次诉讼的目的是变相胁迫被告,如若支持其诉请,无疑是肯定了“以花钱维系婚外不正当男女关系而追求有违公序良俗情感利益的行为”,对被告的家庭而言,无论是情感上还是经济上,都是二次伤害,这也有违我国社会道德伦理。
周某答辩称,曾某所称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双方并没有实际共同生活过,双方之所以经常有约会是因为曾某隐瞒其存在婚姻家庭,故意与我方进行交往,并欺骗我方多次转款给其偿还各种网贷、车贷、房贷、民间借贷等,我方基于以曾某组建家庭、缔结婚姻关系的初衷,才一再相信曾某,并根据其要求多次通过微信转账、银行转账、取现金等方式向其转款高达29万余元。我方自2016年11月份离婚后都是一个人生活,并不存在离婚不离家的情形,曾某的该主张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审法院认定双方系附条件的赠与合同关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应当予以认可,曾某主张的双方的经济交往属于违反公序良俗及道德规则,并没有提供证据佐证,相反我方在2024年4月份发现曾某存在婚姻家庭及同时与多个异性进行交往之后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提出分手,并要求曾某返还该期间向其附条件赠与的款项,曾某也表示愿意退还相应款项,只是基于其经济不宽裕未能及时退还,因此曾某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